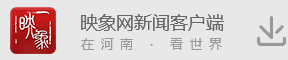深圳程序员年薪25万 和老乡合租"握手楼"
2017年12月30日,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,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,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20天前,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26层跳下,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。
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。在它的周围,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,多数与IT相关。南山区有144家公司上市,资本厮杀的战场上,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。
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,汇聚在南山科技园7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,他们像专业化的螺丝钉,推动高速运转的机器,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,也改变着他们自己。
代码改变命运
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方向一角,在过去38年里,它随着整个经济特区一同,矮屋变高楼、农田变大道、小渔村变大都市。很难说,南山科技园、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,三者谁才是“中国的硅谷”。
由南向北进入南山科技园的标志,是深南大道和大沙河的交汇处的一座沙河大桥,桥身上设计了镂空的1与0的数字组合,也有人称之为二进制桥,意味着通往计算机之路。

夜晚的沙河大桥。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王倩 图
柳莹来到深圳之前,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一串串代码联系在一起。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来自湖南怀化,大专学的是服装设计。CAD(计算机辅助设计)曾是她最爱的一门课程,她喜欢用一根根线条勾勒出模型的感觉,这也成了她当时找工作的方向。
但当满怀期待的她跟随学校大巴来到实习基地时,她看到的是冰冷的铁门,荒凉的工厂,拥挤的集体宿舍。
走进车间,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传送带上是一个个待折叠的纸盒,两边的工人阿姨将纸盒拿起、折叠、放下。除了这个机械的动作之外,她们面无表情、一言不发。
“当时我的心就凉了,我以为会是办公室设计之类的工作。”随后的一周里,她也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单一的动作——拿起、折叠、放下。每天让她疲惫的不是站着工作八小时,而是枯燥麻木的工作给她带来的无力感。那几天,她几乎没说过话,除了上工,她哪也不想去。
一周后,她哭着打电话给父亲,想要回家。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,她工钱也没结算就逃离了工厂。
这次实习经历,似乎让柳莹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毕业后不久,她的表哥在深圳南山打来电话,得知了柳莹的情况后对她说,要不你也来南山吧,跟我学写代码。
那是柳莹第一次听说代码和编程,第一次听闻程序员这个职业。上学期间,她都没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。但柳莹想,反正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工作,去就去吧。
可这一去,她什么也不会,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。
当时表哥留给了柳莹一台陈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,她能学的东西也很有限,“Java后台太复杂学不来,做UI美工我没底子,只能学前端开发”。
每天表哥上班后,柳莹就一个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自学。她对着电脑看着视频,一点一点走进编程的世界。
对她来说,零基础学编程要吃很多苦。由于写代码要用到不少英文词汇,而她的英语很差,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、抄写。好在用的多了,自然也就学会了。
柳莹回忆,自己有时学累学腻了,也会聊天逛网页。被表哥知道后,断了她的网,只留本地视频给她看,这让柳莹的焦虑感骤增。
吃住全在表哥家的柳莹为了减轻负担,有时还会去帮着朋友看店。每个月赚几百元,虽然不多,但她至少吃饭的钱有了。
时间慢慢过去,她始终处于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中,学了真的就能找到工作?
这样的疑问持续了三个月,有天她终于沉不住气问表哥,“我能不能去上班了?”表哥打心眼里觉得,她学的那点东西自己压根看不上,但还是让柳莹试着投投简历。
接下来就是撒网式投简历、跨区域面试的过程。
十家公司里面能有两家回应她就很开心了,虽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仅有3500元,但至少能够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,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。
三年过去,如今柳莹的月薪也过万了,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不上优越,仅仅是一线的普通码农,但对她来说,命运早已在那三个月发生了改变。
她时常会想起那天从工厂里逃走的情景,也会怀念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学代码的日子。

柳莹的工作常态。 受访者供图
“风口上的猪”
在某搜索引擎上输入“程序员”三个字,结果的前几条都是与编程有关的培训广告。为了摆脱贫瘠的生活,不少年轻人通过参加培训班进入IT行业。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在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,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63578 元的年平均工资占据了收入榜首。
这似乎是程序员的最好的时代,也可能是最坏的。
柳莹回忆,2015年,她曾经上午从一家公司离职,下午去另一家公司面试,第二天立马就可以上班。光2017年,柳莹就换过三家公司,一家破产,一家老板跑路。
一面是资本的热流涌动,另一面是创业公司的骤生骤死。进入IT行业六年,雷大同形容一路“摸爬滚打”。
1990年出生的他来自湖南,虽然只有高中学历,已经称得上公司里的“技术大牛”。
这位“大牛”最常的打扮是,上身一件穿旧的深色短袖,下身牛仔裤、皮拖鞋,看起来貌不惊人。他住在南山区西侧宝安区的一处城中村内,狭窄喧闹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“农民房”。
农民房的说法来自于改革开放后,当地人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用于出租。这些房子显得陈旧而又拥挤,被称为“握手楼”,意思是两栋楼挨得很近,楼两边的人甚至可以握到彼此的手。
雷大同和一个老乡合租在一栋农民房的顶层,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衣物、箱子、自行车,25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不大能找到下脚的地方——很难联想到他的年薪有25万。

雷大同的屋子 受访者供图
上学时爱玩游戏的雷大同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。当时“年少无知”的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,“如果我不上大学,一个月挣4000,四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钱?”
他的工作并非是开发设计,而是测试。“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,我就负责玩,玩出bug给他们修复。”
在外人眼里,这是一份看似轻松愉悦的工作,但雷大同说,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。
每当游戏上线或发布新版本之前,所有测试员必须通宵达旦地作业,从早到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,只要一两天就会失去玩游戏的乐趣。
为了节省人力,更高效地进行测试,有人会用脚本让机器自动测试。雷大同也开始跟着学,他心里明白,不学这个,工作就干不下去。
2011年,在某天凌晨加完班后,雷大同泡了一杯柠檬茶,喝了几口就睡了过去,等醒来他感受到剧烈的胃痛袭来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他才去医院检查,诊断结果是慢性糜烂性胃炎。
“我上网查了一下,这是长期熬夜、饮食不规律导致的。”雷大同说。
从那时起,雷大同就慌了,随即辞职,回去开始自学后端开发。每天他什么也不干,早8点睡醒了就开始看视频,一直看到晚上9、10点。
回忆起那段日子,雷大同说,纯粹就是没钱吃饭,又不想问家里要钱,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赶紧学好,毕竟之前的收入也不多,想靠这个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
好在写过脚本的他有些基础,一个月内就把整个Java语言过了一遍。然而等找到工作后他才发现,程序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。
雷大同说,有些互联网公司属于宽进快出的类型,每次招七八个人,最后只留下一两个。为了留下,整个半年他都在加班加点,上班没做完的工作他带回家继续做,那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拼搏岁月。
雷大同信奉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:站在风口上,猪都可以飞。不少人认为,创业找对方向就能赚钱。而对于就业者来说,选对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但雷军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,“没有风的时候,猪怎么办?”
雷大同说,雷军前面那句话没说完,“猪都可以飞得起来的台风口,我们稍微长一个小翅膀,肯定能飞得更高”。
这个“小翅膀”,对雷大同来说可能就是夜以继日的努力,还可能是一纸文凭。
云栖社区做过一份《2017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》,发现中国开发者中58.6%的人是本科毕业,21.8%的人专科毕业,11.9%的人硕士毕业。
像雷大同这样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没挤进调查样本。2017年,他参加了成人高考,就是为了让工资“赶上”自己的能力。
他能明显感觉到,近几年当“风口的风”没那么大时,公司招聘开始设置门槛,要求具备一定学历。有次他去应聘,HR过了,技术顾问过了,部门经理也同意他加入团队,但简历一到老总那发现学历是高中,最后还是将他拒之门外。
这个时候,他特别后悔当时算的那笔账。“现在来看,还是算亏了。”雷大同苦笑着说。